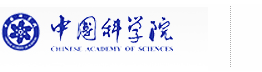叶朝辉简介:叶朝辉是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院士。他长期从事波谱学与量子电子学领域的研究,在建立波谱与原子分子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发展我国铷光抽运原子频标等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固体高分辨及多量子核磁共振研究方面作了系统研究,在国内率先建立了固体高分辨核磁共振的实验设备,研制成功了当时世界上工作频率最高、微波功率最大的动态核极化(DNP)谱仪等磁共振仪器。他曾经担任波谱与原子分子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1986~1993),武汉物理所所长(1987~1996),武汉物理与数学所所长(1996~1999),中科院武汉分院院长(1999~2007)。他现任武汉物理与数学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武汉磁共振中心主任。

武汉磁共振中心外景
“在举国大庆的时刻,路甬祥院长高度概括了科学院的使命:永志创新。我非常赞同。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灵魂,也是中国科学院的神圣使命。回顾科学院60年来所走过的历程,实际上是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科学时报 鲁伟 蔡怡春报道]1961年,波谱学家王天眷研究员在中科院中南物理所(后更名为武汉物理所,现为武汉物理与数学所)创建磁共振波谱学科。经过几代波谱人的辛勤耕耘,当时小小的研究室如今已变身为国家重点实验室,拥有一支结构合理的科技队伍,已经成为国内波谱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时值建国和建院60周年的喜庆时节,记者聆听了波谱学家叶朝辉院士关于波谱学的全景解读。
——“这些年来波谱学的发展非常迅速:它的学科跨度从物理原理、技术方法的确立,到化学和生命医学的应用研究,发展非常快。这是国际上波谱学发展的大趋势。”
《科学时报》:近年来,波谱学得到了非常迅速的发展,它在科学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你能否谈谈这个学科的发展情况?
叶朝辉:我进入到波谱学这个领域是从读大学开始,那个时候我们的物理学里面有一个分支学科,叫波谱与量子电子学。老一辈科学家把微波和射频频段的光谱学称之为波谱学。波谱学的代表是如今被普遍知晓的核磁共振波谱学,简称为核磁共振(NMR)。
这些年来,波谱学发展非常快。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核磁共振领域的科学家已经5次获得了诺贝尔奖。这5项奖实际上代表了波谱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核磁共振领域的科学家获得过两次诺贝尔物理学奖,代表了当时的波谱学研究还处在原理和方法的创造时期;第二个阶段,从事核磁共振波谱学研究的科学家分别在1991年和2002年获得了两次诺贝尔化学奖,这表明波谱学已经在化学学科得到应用,特别是在研究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和动态上,成为一个有力的工具,被广大的化学家掌握和认可;第三个阶段,到了21世纪,核磁共振已经为大众所熟知,在生物、医学上得到广泛应用。核磁共振成像(MRI)已经成为医学界一种无损的、普遍应用的医学诊断和研究的影像工具,所以在2003年,从事波谱学研究的科学家又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有意思的是,获得这个奖的两位科学家,一位是物理学家,一位是化学家。
这就充分说明这些年来波谱学的发展非常迅速,学科交叉的特色十分明显。它的学科跨度从物理原理、技术方法的确立,到化学和生物、医学的应用研究,发展得非常快。这也是国际上波谱学发展的大趋势。
《科学时报》:那么,波谱学在国内又是怎样一种发展状况呢?
叶朝辉:目前,国内该领域的研究相对薄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老一辈的科学家,像虞福春、王天眷、丁渝先生等为创立波谱与量子电子学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但是他们的杰出贡献多是在国外作的。他们回国之后在北京大学和中科院开创了研究基地,可惜大都在“文革”中先后中断。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波谱学研究才重新起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和国外比,依然还处在跟踪阶段。比起其他学科,我们在波谱学上所作的贡献还不够。这说明我们的基础研究还要进一步加强,特别是现在波谱学又和高技术应用紧密联系,这就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路甬祥院长提出要“永志创新”,我觉得波谱学发展尤其应该如此。
——“我所在的研究集体的研究领域已经逐步从物理学科走向了化学学科,并逐渐被化学学科的同行所认可。我自己是学物理出身的,说明与时俱进的创新使命和任务开始挪到了我们年轻一代的身上。”
《科学时报》:能否谈谈你对路甬祥院长提出的“永志创新”的理解?
叶朝辉:今年是新中国建立和建院60周年,在举国大庆的时刻,路甬祥院长高度概括了科学院的使命:“永志创新”,我非常赞同。创新是一个国家、民族生存发展的灵魂,也是中国科学院的神圣使命。回顾科学院60年来所走过的历程,实际上是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在建国初期,国家成立中国科学院,当时的使命就是以国家需求为己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两弹一星”精神就是这个时期的典范。后来进入到改革开放,我们迎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时期,以老院长周光召为代表的中科院党组又提出了“一院两种运行机制”的改革发展模式,鼓励一些有应用开发能力的研究所走向市场,这成为我们日后改革的基础性举措。随着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建设,中国科学院确立了新时期的办院方针,概括地讲就是“两个面向,做三性的工作”。以路甬祥院长为代表的中科院党组带领我们进入国家知识创新工程的试点,迎来了中国科学院新的创新发展时期。回顾整个发展历程,贯穿核心的实际上就是改革和创新。所以,我觉得路甬祥院长“永志创新”的概括非常深刻。
《科学时报》:长期以来,研究所在波谱学研究方面做了哪些创新性工作?
叶朝辉:我们所的磁共振波谱学科是老所长王天眷先生在1961年初创立的。创建初期主要是建立实验条件、培养科研队伍、研制科学仪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在中科院的支持下,学科有了新发展,我们在谱仪研制、实验方法、基础理论以及应用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绩。
1985年,中科院建立首批对外开放的18个研究所和实验室,我们作为波谱学研究的一个点进入到其中。虽然开始非常艰难,但是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最终发展成为波谱与原子分子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这应该是我们研究所在国家层面为推动波谱学的发展作出的有代表性的一个贡献。
2008年,以波谱与原子分子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磁共振部分为基础的武汉磁共振中心正式挂牌。这个中心作为全国13个国家科技条件平台建设项目之一,现已成为为全国波谱学提供支撑和服务的平台,同时也是波谱学的研究和技术开发的基地,未来将进一步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开放共享、多学科(物理、化学、生物学、医学)交叉的以核磁共振技术为主的科学研究、技术支撑、学术交流和交叉型人才培养的国家级综合科学平台。
今年,我们的波谱学研究团队成功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资助。这是我非常看重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创新群体属于分析化学学科,也就表明我们的研究已经逐步从物理科学走向了化学科学,并逐渐被化学同行所认可。我是学物理出身的,我们的波谱与原子分子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归类在物理科学的。我们波谱学的研究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有一个学科的发展与重新定位的问题。获得基金委化学科学部的创新群体这件事说明,新形势下与时俱进的创新使命和任务挪到了我们年轻一代的身上。
科学在发展,科学本身的体系也在不断演变。我们下一个布局很可能是以生命科学为牵引,逐步使波谱学研究走进生命科学领域。相关的数据表明,生命科学(脑科学和蛋白质科学)逐渐成为核磁共振波谱学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领域。目前,我们积极地做了一些有成效的工作,但是面临的形势还十分严峻,需要大家不断努力。
——“现在的情况是,先进科学仪器全部被国外的大公司垄断,竞争很残酷,如果放弃,我们永远没有机会。只要我们坚持走下去,哪怕比它们产品的性能低,但是我们拥有这个技术后,它们对中国的市场就会重新评估。”
《科学时报》:你认为波谱学从物理学科到化学和生命医学的跨越,其主要驱动力是什么?
叶朝辉:主要是两个,科学和市场。市场就是科学仪器的市场。大体上,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都应该是这样:先是探索自然和发现规律,然后才是应用,应用就会产生效益,反过来又推动学科发展。
波谱学也是如此,先从科学到原理,再到实验方法,从实验方法里又会产生出来一些技术和仪器装备,最终形成一个产业。形成一个从科学技术到装备产业的链条,好的科学仪器反过来又给科学研究提供有利的工具,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如果说10年前提到核磁共振民众还很陌生,现在它已经成为医院非常常见的诊断用的影像仪器了。前些年有人就作过统计,仅超导核磁共振仪在全世界的医院里就超过2万台。据此,可以推算出每年全世界的医院使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进行诊断的费用超过600亿美元,这个市场非常大。此外,实际上核磁共振仪器市场还有另外两个不太为大众了解的方面:一个是核磁共振波谱仪,另一个是核磁共振石油测井仪。这两种科学仪器也有可观的市场规模。
所以,只要某个学科产生的高技术形成一定的生产力,它就会反过来推动这个学科的发展,一旦形成这样一个循环,它的生命力就会非常强大。
《科学时报》:你们在仪器研制方面作出了哪些有益探索?
叶朝辉:我们过去在老一辈科学家的努力下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后来也走过一些弯路,这也是值得我们现在反思和探讨的一点。
过去,因为科研经费紧张,没有钱去买仪器,大家要开展研究就必须自己动手建立仪器装备。当时,我们完成了60MHz核磁共振谱仪的改造,研制成功100 MHz核磁共振谱仪氘锁系统和360 MHz超导核磁共振谱仪,还研制成功80MHz~54GHz动态核极化谱仪等,应该说是做了不少工作。改革开放以后,发现国外的仪器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就花钱买呗,结果就把仪器自主研制给丢掉了,不做了。现在,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新仪器和新技术是创新的重要源泉。你不自主研制仪器,就往往拿不到原创性的东西。
值得庆幸的是,2006年,我们承担的“300MHz~500MHz核磁共振波谱仪的研制”课题获“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科学仪器设备研制与开发”项目的支持。可以说是在国家的支持下,我们又把丢掉的这一块给重新捡了起来。
该课题进展到现在接近3年了,我们做得非常艰苦,课题组的老师和同学都很努力,但是遇到的困难比想象的大得多。因为别人已经发展得很快、很先进了,我们不仅要把别人的东西学会,消化吸收再创新,更要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路来,确实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我个人现在也倍感压力。最大的担心还是我们重新做出来的仪器不能满足国家的要求、不能圆满完成任务。当然再艰难,我们也要去尝试,要走出一条路来。我们的产品型样机预计今年年底可以出来,虽然现在我们不敢说非常成功,但是我们努力了。现在的情况是,先进仪器全部被国外的大公司垄断,竞争很残酷,如果放弃,我们永远没有机会。只要我们坚持走下去,哪怕比它们的产品性能低,但是我们拥有这个技术后,它们对中国的市场就会重新评估。
《科学时报》:你们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你觉得破解这种困境的关键在哪里?
叶朝辉:我个人认为,在目前和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国内波谱学研究还处于跟踪阶段,总体局面不容乐观。破解这种局面最核心的因素是人才,特别是领军人才。目前国内的基础研究也在发展,从国外归国的人越来越多,逐渐聚集了一批精英人才。以我们波谱学的研究集体为例,我们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先后得到了5项杰出青年基金资助:毛希安和邓风在物理化学学科,刘买利和唐惠儒是在分析化学学科,徐富强在生命科学学部。现在国家的各种“人才计划”也很多,我们要抓住现在的有利时机,努力引进和培养领军人才还是大有可为的。
《科学时报》 (2009-10-13 A2 庆祝中国科学院建院60周年系列报道)